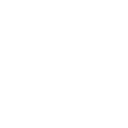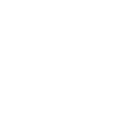Pinnacle平博体育(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靴子落地!4月21日,中国排球协会发布声明,称因为排超联赛的商务运营推广合作伙伴体育之窗长期拖欠排超联赛的运营推广费用,所以自4月14日起解除合作关系。其实,2019年业内就有体育之窗运营排超联赛后继乏力的传闻。但在体育产业日趋回归冷静、裸泳者遍地皆是的大背景下,这些传闻在江湖闲话中已激不起一丝涟漪,相反,当年一起参与竞标的同行们在感慨中带着几分钦佩:“鉴于体育之窗投资排超的力度那么大,能撑这么久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面对排超这么一个在中国仅次于中超和CBA的第三大体育联赛,排协渴望让排超直追中超和CBA的决心毋庸置疑,签下5+N合同、平均每年运营费用一亿元的体育之窗更是无比渴望做强做大联赛,但最终,主管协会和商务运营推广商却只能选择不体面地分手。面对这种残局,体育之窗固然有很多可供指摘之处,但体育之窗却绝非唯一的输家。在目睹了体育之窗的下场后多少同行会引以为戒甚至心生悲凉,排超未来的商业价值大概率会缩水,更可怕,这种对本土体育IP无法盈利的绝望和无助会在整个体育产业蔓延,放任其蔓延下去,最终受害的是每一个中国体育产业人。
这桩案例留给行业的除了一声叹息外,更多的则是虽然惨痛但却发人深思的拷问:在本土顶级体育IP产权国有的大背景下,第三方运营公司如何精准报价,从而确保中标后自身能够实现盈利?中国单项体育协会在为联赛选择合作伙伴时,是否也应该在评标时核算出一个合理的价格指导范畴,从而为竞标单位留出盈利空间?在资本热情逐步退却、体育产业退潮大势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下,主管协会和运营公司又该如何妥善处置早年头脑发昏时签下的天价合约?后来者又该如何签订一份真正能够实现多方共赢的运营代理合同呢?
时间回到2016年7月,当时体育产业有多疯狂?就在一年前,体奥动力用5年80亿元的天价斩获了中超公共信号制作权,就在同年,乐视体育完成了超过80亿元的B轮融资。在这种大背景下,每一个本土体育IP的价值都被无限放大。恰逢此时,排球联赛与中视体育为期10年的合作到期,排协早早就在2016年3月7日发布公告,公开征集排球联赛新一期的商务运营推广合作伙伴,此后掀起了一场为期三个月、多达七家公司参与角逐的排球联赛竞标大战。
排球联赛创立于1996年,与1994年起步的中超(前身是甲A足球联赛)、1995年创立的CBA(前身是甲级篮球联赛)份属同辈,中国又向来强调“三大球”这一概念,所以排球联赛这个原本并不特别受关注的IP在2016年也收获了一大批追捧者。2016年3月30日,排协宣布共有7家企业通过了初审:北京一智超跃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盈方体育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盛力世家(上海)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欧迅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中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体育之窗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但盈方中国很快退出竞标,此后进入首轮应征谈判程序有5家公司:盛力世家、欧迅体育、中视体育、中奥体育、体育之窗。
如今排协的公告黑纸白字指出,早在2017-2018赛季体育之窗就开始拖欠款项。要知道,2007-08赛季仅仅是体育之窗运营排球联赛的第二个赛季。显然,体育之窗不仅没有找到盈利模式,而且也高估了自身的资金储备能力。当资金链断裂又找不到盈利模式时,拖欠联赛运营费用已不可避免。鉴于体育之窗从2017-18赛季就就已开始拖欠费用,中国排协拖到2020年4月才宣布解约,可想而知,这期间发生过多少不为人知的催款和谈判,在最终催款无望后,排协才无奈选择了这种看似不体面但舍此别无他法的分手方式。
面对这些典型的中国式问题,想要找到真正的解决之道并对未来的中国体育产业形成启示,或许我们可以从以往中国本土联赛的一些非典型案例中找到答案。毕竟,国外的顶级职业体育联赛运营方都是联赛所有俱乐部老板联合投资成立的联赛运营公司,联赛产权属于所有老板,运营权也属于联赛公司。而中国目前的大多数顶级体育赛事的产权都属于国家体育总局旗下的各个项目运动管理中心或者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旗下的各个单项体育协会所有,换言之,体育赛事产权国有。但与此同时,这些协会受限于种种原因,又无力去直接组建联赛公司,最终只能将产权和运营权分离,通过招标将联赛运营权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如你所知,中超和CBA在创立初期,也都曾将商务运营权授予美国体育公司IMG。
对于体育之窗这些第三方运营公司而言,在与联赛签约时,必须做好三方面的功课:第一、建立一个相对科学的联赛商业潜力评估体系,从而测算出该联赛投入成本和盈利空间,只有测算出这些指数,才能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第二、获得联赛运营权后,必须尽可能将合同年限拉长,只有足够漫长,才能确保前期的投资转化成的果实最终为你所有,而不是被别人摘走果实;第三、一旦在实操过程中发现此前报价过高,盈利空间不足,一定要及时沟通,要求修改合同,必要时宁可主动终止合同。
对于市场开发成果处于开拓初级阶段的联赛而言,想要在短期内盈利,基本属于痴人说梦,即便是如今吸金能力位居全球前列NBA,自1946年创立后的联赛发展前三十年,整个联赛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不少俱乐部都挣扎在破产边缘,简而言之,体育这门慢生意往往先苦后甜,在漫长岁月的洗礼下往往才能吹尽黄沙始得金。所以,对于中超、CBA、排超这些中国本土联赛的第三方运营公司而言,必须精准评估出可以盈利的报价方案,一旦签约则要尽可能争取最长的签约周期。
要知道,时任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已经56岁,距离60岁退休仅剩4年时间,盈方要求的合同长度明显超出了他的任职时间。几经协调,最终报请体育总局备案,这才同意与盈方签下了一份7+5、总长度达到12年的CBA商务运营推广合同。但篮协也有两个附加条件:第一、合同在履行完前七年后,篮协可以选择跳出合同重新招标;第二、650万美元只是基础联赛运营费用,如果盈方实现盈利,那么利润层面也应该给篮协进行分成,为监督CBA的商务营收状况,当时篮协还和盈方共同成立了一个中篮盈方体育公司。
事实证明,盈方在运营CBA联赛早期确实连年亏损,以致于盈方中国当时的运营团队被大量解雇,王应权本人在2008年也被迫离职。但此后马国力走马上任,在他的掌控下,盈方中国从CBA的2009-2010赛季开始扭亏为盈,此后马国力又在2012年成功续约五年。整体来看,盈方中国运营CBA的12个赛季中有8个赛季是盈利的,整体来看,无论是盈方本身、CBA联赛还是中国篮协,在那些年里整体收入都是在稳步上升,所以盈方运营CBA长达12年这一案例堪称经典。
但如你所知,彼时的男足成绩萎靡不振,除了北京奥运会外,其余国际大赛的参赛机会更是寥寥无几,世界杯预选赛更是早早出局。没有比赛作为载体,赞助商对男足自然不感冒,盈方亏得一塌糊涂,王应权最终下课。此后,马国力决定快刀斩乱麻,尽快解决这一遗留问题。他最初希望足协能同意修改合同,改成弹性合同,但在与足协沟通无果后,盈方干脆单方面宣布解约,此后还以国足成绩太差、比赛太少为由要求索赔,最终自知理亏的足协很快就同意了解约。
如你所知,排超为了国家队备战东京奥运会此前曾直接将主客场制改为赛会制,而乒超、WCBA等联赛更是宣布为各自项目所属的国家队的东京备战任务直接取消赛季。这直接导致国家队商业价值高,而联赛乏人问津,在这方面,乒、羽、女排尤其突出。换言之,联赛和国家队的商业价值出现倒垂倒挂现象。而遍观国外体育产业发展规律,联赛和国家队是正向关联的关系,联赛商业价值最高,联赛造就体育明星,最终通过明星将商业价值辐射给了国家队。
如前文所言,2005年中国篮协将CBA运营权授予盈方,而在2006年在对中国男篮的商务运营权进行招商时,盈方意识到如果国家队运营权旁落他人,尤其是被做事风格强势无比的NBA所获得,可能会对自己运营CBA带来种种干扰。为此,盈方豪掷1年1500万的超高报价,同时愿意打包接下商业价值并不高的中国女篮,最终说服篮协将中国男篮的商务运营权也授权给了盈方。而盈方凭借着CBA和中国男篮这两大IP,成功实现了对中国篮球招商赞助体系的垄断,从而形成规模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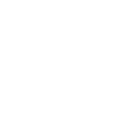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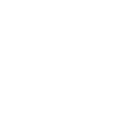
@HASHK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