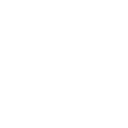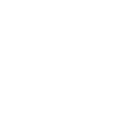Pinnacle平博体育(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中国由一个个区域组成,每个区域各具特色,都对“全局”有所贡献,区域研究要摸清区域内部的结构与变迁,在此基础上作“跨区域”研究,并将区域与“全局”的联系揭示出来。有些人认为,对“全局”的研究“高于”区域研究,这是十分狭隘的观点,对认识“何谓中国”“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十分不利。与此同时,区域研究若能重视“区域”与外部的互动与联系,政治史与人物研究若能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或可避免过度“碎片化”的弊病。
在广州府所属南海、番禺、顺德、香山等县,至迟从明末开始即出现了“不落家”(归宁不返)现象,随后也扩展到肇庆府。因广州、肇庆文化差异甚少,本文的“广府”包含广州、肇庆两府。所谓“不落家”,即女子结婚后仍长住娘家,只在重要节日或翁姑生日时在夫家住宿一两天。从事反清复明运动的著名诗人屈大均是番禺人,他的发妻即实行“不落家”。这一风俗的起源,学界至今未能得出一致结论,我个人认为与古越族女子地位较高的传统有关。不管其起因如何,这种风俗到清代已经带有包办婚姻、家庭专制的意味。1900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日报》刊出《男女平等之原理》一文,注意到“不落家”是对包办婚姻的抵抗。该文指出:“今居中国,男不识女,女不识男,互昧平生,强作婚姻,非其志也,迫于礼已。其或不顺,势必至男则休妻再娶,女则归宁不返。”
在传统中国,女性姓名权并非普遍的法定权利,有一定上层社会的女子会有完整姓名,庶民女子则长期没有这个权利。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女子,如班昭、蔡文姬、李清照等,是以其史学、文学成就名世,梁红玉、秦良玉等则以军事才能而著称。其他许多女子,多作为妃嫔、妻妾、名妓而传世。以改良棉纺织技术著称的黄道婆,按笔者的理解“道婆”并不是她的本名,而是因她信仰宗教,故而别人对她如此称呼。庶民阶层的女子,在法律文书及其他正式场合,未嫁女以“X氏女”出现,已婚女子以“X门Y氏”“XY氏”出现,或者在父姓、夫姓后面加上“X娘”“X姐”,实际只是排行,并非现代社会的正式名字。汉唐宋元时期,礼法尚未曾十分严苛,偶尔也有一些碑刻中庶民女子使用姓名全称的例子。到了明清时期,理学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男权社会达到顶峰,庶民阶级中女子姓名权更加衰落。
暨南大学刘正刚教授,释读了广州黄埔村嘉庆十八年(1813年)《重修洪圣宫殿碑记》,发现其中梁氏家族部分有“花女梁玉藏助金一员、花女梁观平助金一员、花女梁配莲助金一员……”等26条记录,而胡氏家族的“花女”则有29名。这些名字都非常正式,与现代女性名字相类,并非以前“梁八娘”“梁八姐”那样的排行称谓。广东省社科院陈忠烈研究员依据田野调查做了解读,认为“花女”指未婚女性,碑文中的“花女”应该大多数指的是不愿意结婚的自梳女。
张竹君(1879-1964),广东番禺县沙湾螺阳乡岐山村人,出生于十三行行商家庭。十三行行商为清政府授权的外贸商人,专门与来华贸易的西方人打交道,见识通达。张竹君少时入教会所办的博济医院学习西医,1900年1月毕业后,即创办南福医院于广州,医院的建设费、开办费应有部分来自家庭的支持。张竹君奉行“不嫁主义”,主张女性自立自强,跟她出生成长的地域有重要关系。沙湾所在的番禺禺南地区,与相邻的顺德、南海、香山各县,乃是“不落家”、“守清”与“自梳”风气最为盛行的地区。
在博济医院期间,张竹君也从来自美国的两位女医生富马利(Mary Hannah Fulton)、赖马西(Mary West Niles)身上,学到女性独立自强之道。从1886年开始,赖马西医生负责管理博济医院女病房,同时收养了一批女盲童加以教养,进而建立华南地区最大的盲童学校明心书院。她还奉行不嫁主义,一直在广州服务到年老退休。1899年,富马利医生独立筹款,在广州西关创办中国第一家女子医学院夏葛医学堂,与张竹君保持着长期的师生友谊,1915年因病到上海休养,与张竹君携手创建上海第一家粤语教堂。
1901年,张竹君在广州河南创办南福医院,在主持医疗事务外,主持演说会,倡议兴办育贤女学堂,“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其时胡汉民任《岭海报》总主笔,对张竹君的女权运动赞襄最力,几乎将《岭海报》变成张竹君的机关报。胡汉民一度东渡日本留学,不久又回粤,继续编辑《岭海报》。其时《羊城报》记者莫任衡对张竹君等人言行不满,写成《驳女权论》。胡汉民与张竹君相善,乃与《亚洲报》主笔谢英伯相约,联手向《羊城报》反攻,扶持女权运动。张竹君常在夏秋之际,雇一只紫洞艇(陈设豪华之花舫)停在珠江边,以为纳凉之所,胡汉民常与友人到艇上叙谈。1904年,张竹君前往上海,先后创办女子兴学保险会、育贤女学堂、女子中西医学堂、上海医院等,在女子教育、医疗、互助救济方面开创出宏大事业。
1908年,胡汉民留日期间,在法国《新世纪》杂志发表《粤中女子之不嫁者》,一反士大夫对自梳风气的抨击,率先加以肯定,指出“以为世界可哀可敬者,莫此等女子若也”,认为不落家、自梳是对野蛮礼教的反抗,“乃真野蛮恶风所生之反动力也”,肯定其抵抗包办婚姻、解决经济独立、组成团体以抵抗社会压力的重要意义。最后,他对女权问题提出四点意见:一是男女不自由配合为大逆人道;二是经济革命而后男女可以平等,顺德等地自梳女因从事丝业得以独立维生,故能历久不衰;三是女子抵抗强权之能力不弱于男子;四是强者每怀私利以弱者之抵抗为非理。可以说,以孙中山、胡汉民为首的革命派,比维新派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致力于表彰女子追求独立的反抗精神,尤其重视经济独立对于女权运动的意义。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张竹君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自任会长,组织医疗队前往武汉进行战场救护,并掩护黄兴等同盟会高级干部成功抵达武汉。几乎同时,广东光复,胡汉民出任广东军政府都督。他在组织广东省临时省议会时,为确保有一定人数的女性当选省议员,胡汉民主持拟定议员选举法时,特制定比例代表制,确定同盟会代表名额20人,男女各半,故而顺利选出议员程立卿、李佩兰、廖冰筠、邓惠芳、张沅、伦耀华、庄汉翘、易粤英、汪兆锵、文翔凤10人。这是中国女子正式参政的起始,在全亚洲也属于创举。
经起草委员会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1930年12月3-4日,民法亲属篇与继承篇在立法院获得通过。亲属篇规定,女子无论结婚与否,对个人之财产有完全处分的权利;任何权利,均不应男女而有所区别;无论男女,均有资格担任家长。与此相应,《民法》继承篇赋予无论婚否之女子对父母遗产均有继承权、寡妻对丈夫遗产有继承权,革了宗法制度的命。这部民法,是全世界第二部规定男女平等的民法典,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与之相比,日本民法仍对女子权利有诸多限制。
何香凝在女子参政方面取得的成就,并非偶然,其渊源是清中期以来广府地区渐次兴起的“自梳”运动、“不缠足运动”以及清末以来的女权运动。何香凝出生于南海县一个富商家庭,在香港长大,自小即不缠足,这在内地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她能够坚持下来,与广府地区“不缠足运动”的开展有着直接关系。民国初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在广州百子路(今中山二路)购置洋楼两座,购房款全部出自何香凝,这笔巨款来自何所继承的遗产。虽然当时的法律否定外嫁女有继承权,何家主事人仍认为何香凝有权继承部分遗产。蒋介石在广州市区的住所,正是借用何香凝出资购买的其中一座洋楼作为公馆。
近年来,有关近代女权运动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多集中在留日学生界、江浙沪、湖南等地,对广府地区重视不足。正是在广府地区,自梳运动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为女性获得财产所有权与支配权开拓了广阔空间,女性也得以抛头露面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有力地支援了辛亥革命。张竹君的闺蜜徐宗汉,以富家寡媳身份加入同盟会,以奁产投充革命经费,在“黄花岗起义”时护送受伤的黄兴前往香港疗伤,而后缔结连理,乃是亘古未有之惊人举动。胡汉民妻子陈淑子、胞妹胡宁媛,在同盟会多次起义中舍生忘死,扮作新娘用花轿运送枪械,其胆识也不可多得。
妇女运动领袖中,妇女部长何香凝(广东南海)、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沈慧莲(广东番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伍智梅(广东台山),首届“国大”代表邓不奴(广东三水),青年军女青年服务队总队长陈逸云(广东东莞),都是广府人。方面,大革命时期杰出的女党员谭竹山(广东高明)、陈铁军(广东南海)、区梦觉(广东南海),也来自广府地区。没有晚清以来广府地区广泛深入的女权运动为基础,不可能涌现出如此之多的妇女领袖。
中国女子姓名权、财产权,并非完全外来的产物,而是在清中期的珠江三角洲萌芽、发育、发展,一代代自梳女结成生死与共的“金兰”团体激烈抗争所取得,为此也付出惨重代价。她们历经奋斗而取得的女子财产权成果,为民主革命时期广府地区女权运动、女子参政运动铺平了道路。女权领袖张竹君对胡汉民的深刻影响,随着胡汉民入主中枢,而在1930年的民法立法中体现出来,惠及于全国。张竹君推动女权运动的基本策略,是联合“以平等待我”的男性共同奋斗,例如她创办上海育贤女学堂、中西女子医学院,主要依靠绅士李平书的财力支持。同时代的个别女权领袖依靠煽动仇男情绪来博取掌声,对推动平权不仅不利而且有害。
笔者认为,区域研究与“全局”研究同样重要,不了解区域,也难以理解“全国”。曾经,经济社会史研究试图以某个地域为“典型”来“代表”全国,近年来这种过于的狭隘思路如今已有所改变。正如刘志伟所说,没有什么“典型”“代表性”,有的是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区域”,区域的划分也不必固定,可根据研究选题而调整,甚至可以跨越国界。社会史的研究,不存在什么固定的“中心”与“边缘”之分,凡是学者所深耕地域就是“中心”。就我所知,近代跨越省界的民间信仰团体,有不少起源于西南而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催生了数量庞大的民间慈善团体,并延伸到港澳东南亚华人社会;不能因为西南曾经交通不便、经济不如东部发达而不加重视。华南区域研究,是视野的拓宽、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并非要以华南作为什么“典型”,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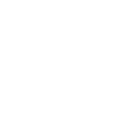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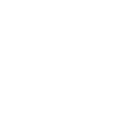
@HASHKFK